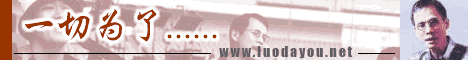
罗大佑:音乐是心灵沟通最有力的媒体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7月29日· 新京报文化副刊 创意一直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从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至今,台湾流行音乐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罗大佑:20世纪60年代是嬉皮士的年代,拿起一把木吉他,披头散发,一副“披头士”的样子,打破传统礼教,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赤裸上身,只有牛仔裤,那是最解放的年代。
台湾的校园民谣时代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沉积,到70年代之后,主要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大家都希望能唱自己的歌,而不是一拿起来都是西洋老歌曲、日文歌曲,于是从70年代开始,慢慢地摇滚乐、重金属都进来了,一直到80年代,迪斯科也进来了。声音要跟“肉”结合在一起,音乐要“跳”。90年代则是各种文化聚合在一起,21世纪我就搞不清楚了,但创意一直是这些年来台湾乐坛最重要的。
寻找久远的认同感
新京报:你即将在北京开的演唱会起名为“之乎者也”,跟你1982年首张专辑同名,似乎有把观众的视线引回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
罗大佑:1982年我的首张专辑叫《之乎者也》,是对当时封建、八股的反讽,所以我会唱《鹿港小镇》这些歌曲,为的是让风气开放一点。可现在是充斥着电脑、手机的时代,当时代把我们强烈地往前推的时候,我们总感觉有点失落,就像我说过的:“这是一个科技的年代,所以我们要找回人性。”电脑、手机用得越多,你的神经越被孤立掉,最好的网站也会让你迷失。
尽管“之乎者也”这四个字我们不会再用,但这时候走回里头,我们总能找到一种久远的认同感,我们应该寻回自己的根。人是不能忘了老祖宗的,你不觉得这古铜色的四个字在21世纪散发出新的光芒吗?
新京报:这样会不会显得有些说教,你有没有考虑过当前内地年轻人和台湾乐迷对音乐需求的不同?你的《现象七十二变》今年初被选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曲目,对自己的流行音乐进入教科书的行列,你有何感想?
罗大佑:我不怕说教,我的年纪随着时间不同,观众也会不一样,在时间的转换里找到一种认同感是最重要的。有人说,我说的比唱的多,那无所谓,因为也是一种沟通。两年半后我重回北京,我知道这个都市的气质对我是种考验,但我有备而来。至于《现象七十二变》入选的事,我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现在我已经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心情,给十六七岁的高中生写歌了,我只相信,音乐是人与人心灵沟通最有力的媒体,音乐之外我还没找到更好的。
音乐被过分制作了
新京报:你写歌30多年,用你的眼光来看,现在台湾乐坛与以前相比,主要问题是什么?
罗大佑:以前是大家“拷”不到李宗盛、罗大佑音乐的问题,现在是CD太多,找不到音乐的问题,音乐被过分制作了。
我的人生正好经历了音乐史上最大的革命,1980年代,MIDI音乐数位转换的出现,使无论什么声音都可以用电子来磨合,从此,科技改变了音乐界几千年的景观。我们跨越了那么多东西,能够活下来其实就不容易。歌手站在台上,其实是有责任“八股”一点的,刚才我把吉他的弦剪剩两根,也是想让大家听到中华民族最根源的声音———也就是两根弦的声音。
这个时代替换太快,全世界的流行歌曲,没有一首的循环是超过一两年的;手机一年左右完全更新了,功能更多、画面更大。我们受到的刺激太多,现在的小孩子,如果要让他们开心,还不如买一个好的电动玩具给他们。但我还是一路在写歌,我知道写歌30多年会有多辛苦,但我有责任感,不能背叛自己的热情,背叛公众对自己的期望,这样我宁愿不去照顾年轻一代的乐迷。你知道写歌从20世纪写到21世纪有多困难吗,前段时间连战、宋楚瑜不是访大陆吗,他们等了50多年。
刚才有人送我生日礼物:1954年的《人民日报》,头版消息是“东北大麦高粱的产量特别好”,下面一小块“闽江匪帮”正在如何如何,隔了51年台湾和内地终于不用这种方式对抗了,真是一大进步。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你到现在都自认为是“斗士”,你对台湾的现实不满,并在音乐创作上注重社会责任感,你在乐坛有多少这样的同行者?
罗大佑:其实我一直很紧张,面对大家时,话要说对,唱歌的时候不能走调;但又不能只讲话,还得有些表演。我对自己的嗓子没法要求,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对自己音乐里的感情有所交代。我对台湾的社会现实一直不满,也等于我一直对自己不满。陶喆和周杰伦的音乐都不错,香港由于语言的关系,还没发现很多我的同行者。音乐人代表了一代又一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不同的偶像,播放音乐的载体也不一样,这是可喜的,最怕是一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新京报:你一直怀着社会责任感、有意拓展歌曲的思想性,但流行音乐自身的局限性会不会阻碍你的创作往深度去发展?
罗大佑:流行音乐一定有局限性,如果不是大街小巷在唱,媒体在不停播放,感觉就不叫流行。
但重要的是音乐没有局限性,从人呱呱落地,“呱呱”的啼哭声就是音乐,而人死了之后,会有送终的丧礼音乐,因此,音乐会一直陪伴我们一生。
新京报:你前段时间到内地采风,对于你或者你的同行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如何看待?
罗大佑:这年头采风已经不太可能了,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在山上走了四个钟头,忽然听到一段音乐,我感觉:“哇太棒了,真正的民歌!”上前一看,才发现是电视的主题曲。我相信音乐是来自土地的,因为人本身就来自土地,虽然早一点的说法是,人是从海里爬出来的,但从海里爬出来以后也要着陆了才能成长。
现代人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我需要多沾染点土地的气息。1993年我去过一个音乐研究所,看到他们搜集了庞大的民族资产,那就是一个民族所需要找的最好的东西。我一直认为人不是走向“饶舌”的,我指的是像爵士乐、古典音乐等大家不熟悉的东西,而是要回到根源上去。我希望我们写的歌,不需要区分哪个阶段,就像我们听到贺绿汀写的《天涯歌女》时,不会觉得这首歌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因为它已经是整个民族的一部分。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罗大佑:音乐是心灵沟通最有力的媒体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7月29日· 新京报文化副刊 创意一直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从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至今,台湾流行音乐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罗大佑:20世纪60年代是嬉皮士的年代,拿起一把木吉他,披头散发,一副“披头士”的样子,打破传统礼教,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赤裸上身,只有牛仔裤,那是最解放的年代。
台湾的校园民谣时代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沉积,到70年代之后,主要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大家都希望能唱自己的歌,而不是一拿起来都是西洋老歌曲、日文歌曲,于是从70年代开始,慢慢地摇滚乐、重金属都进来了,一直到80年代,迪斯科也进来了。声音要跟“肉”结合在一起,音乐要“跳”。90年代则是各种文化聚合在一起,21世纪我就搞不清楚了,但创意一直是这些年来台湾乐坛最重要的。
寻找久远的认同感
新京报:你即将在北京开的演唱会起名为“之乎者也”,跟你1982年首张专辑同名,似乎有把观众的视线引回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
罗大佑:1982年我的首张专辑叫《之乎者也》,是对当时封建、八股的反讽,所以我会唱《鹿港小镇》这些歌曲,为的是让风气开放一点。可现在是充斥着电脑、手机的时代,当时代把我们强烈地往前推的时候,我们总感觉有点失落,就像我说过的:“这是一个科技的年代,所以我们要找回人性。”电脑、手机用得越多,你的神经越被孤立掉,最好的网站也会让你迷失。
尽管“之乎者也”这四个字我们不会再用,但这时候走回里头,我们总能找到一种久远的认同感,我们应该寻回自己的根。人是不能忘了老祖宗的,你不觉得这古铜色的四个字在21世纪散发出新的光芒吗?
新京报:这样会不会显得有些说教,你有没有考虑过当前内地年轻人和台湾乐迷对音乐需求的不同?你的《现象七十二变》今年初被选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曲目,对自己的流行音乐进入教科书的行列,你有何感想?
罗大佑:我不怕说教,我的年纪随着时间不同,观众也会不一样,在时间的转换里找到一种认同感是最重要的。有人说,我说的比唱的多,那无所谓,因为也是一种沟通。两年半后我重回北京,我知道这个都市的气质对我是种考验,但我有备而来。至于《现象七十二变》入选的事,我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现在我已经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心情,给十六七岁的高中生写歌了,我只相信,音乐是人与人心灵沟通最有力的媒体,音乐之外我还没找到更好的。
音乐被过分制作了
新京报:你写歌30多年,用你的眼光来看,现在台湾乐坛与以前相比,主要问题是什么?
罗大佑:以前是大家“拷”不到李宗盛、罗大佑音乐的问题,现在是CD太多,找不到音乐的问题,音乐被过分制作了。
我的人生正好经历了音乐史上最大的革命,1980年代,MIDI音乐数位转换的出现,使无论什么声音都可以用电子来磨合,从此,科技改变了音乐界几千年的景观。我们跨越了那么多东西,能够活下来其实就不容易。歌手站在台上,其实是有责任“八股”一点的,刚才我把吉他的弦剪剩两根,也是想让大家听到中华民族最根源的声音———也就是两根弦的声音。
这个时代替换太快,全世界的流行歌曲,没有一首的循环是超过一两年的;手机一年左右完全更新了,功能更多、画面更大。我们受到的刺激太多,现在的小孩子,如果要让他们开心,还不如买一个好的电动玩具给他们。但我还是一路在写歌,我知道写歌30多年会有多辛苦,但我有责任感,不能背叛自己的热情,背叛公众对自己的期望,这样我宁愿不去照顾年轻一代的乐迷。你知道写歌从20世纪写到21世纪有多困难吗,前段时间连战、宋楚瑜不是访大陆吗,他们等了50多年。
刚才有人送我生日礼物:1954年的《人民日报》,头版消息是“东北大麦高粱的产量特别好”,下面一小块“闽江匪帮”正在如何如何,隔了51年台湾和内地终于不用这种方式对抗了,真是一大进步。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你到现在都自认为是“斗士”,你对台湾的现实不满,并在音乐创作上注重社会责任感,你在乐坛有多少这样的同行者?
罗大佑:其实我一直很紧张,面对大家时,话要说对,唱歌的时候不能走调;但又不能只讲话,还得有些表演。我对自己的嗓子没法要求,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对自己音乐里的感情有所交代。我对台湾的社会现实一直不满,也等于我一直对自己不满。陶喆和周杰伦的音乐都不错,香港由于语言的关系,还没发现很多我的同行者。音乐人代表了一代又一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不同的偶像,播放音乐的载体也不一样,这是可喜的,最怕是一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新京报:你一直怀着社会责任感、有意拓展歌曲的思想性,但流行音乐自身的局限性会不会阻碍你的创作往深度去发展?
罗大佑:流行音乐一定有局限性,如果不是大街小巷在唱,媒体在不停播放,感觉就不叫流行。
但重要的是音乐没有局限性,从人呱呱落地,“呱呱”的啼哭声就是音乐,而人死了之后,会有送终的丧礼音乐,因此,音乐会一直陪伴我们一生。
新京报:你前段时间到内地采风,对于你或者你的同行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如何看待?
罗大佑:这年头采风已经不太可能了,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在山上走了四个钟头,忽然听到一段音乐,我感觉:“哇太棒了,真正的民歌!”上前一看,才发现是电视的主题曲。我相信音乐是来自土地的,因为人本身就来自土地,虽然早一点的说法是,人是从海里爬出来的,但从海里爬出来以后也要着陆了才能成长。
现代人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我需要多沾染点土地的气息。1993年我去过一个音乐研究所,看到他们搜集了庞大的民族资产,那就是一个民族所需要找的最好的东西。我一直认为人不是走向“饶舌”的,我指的是像爵士乐、古典音乐等大家不熟悉的东西,而是要回到根源上去。我希望我们写的歌,不需要区分哪个阶段,就像我们听到贺绿汀写的《天涯歌女》时,不会觉得这首歌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因为它已经是整个民族的一部分。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 欢迎光临 罗大佑音乐联盟网论坛 (http://luodayou.net/bbs2/)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