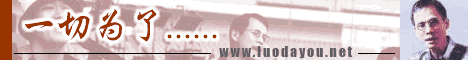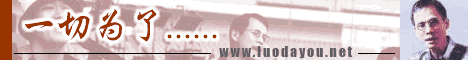
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传奇歌手胡德夫:世上再没有比音乐纯洁的东西 [打印本页]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6-7-18 11:58 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传奇歌手胡德夫:世上再没有比音乐纯洁的东西
传奇歌手胡德夫:世上再没有比音乐纯洁的东西
出道30多年仅出了一张唱片,他的演唱会却是台湾文化人及各路政治人物出席得最多的
★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6年台湾金曲奖的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颁给了一位叫胡德夫的人。这位银发满头、身形矮壮的卑南族歌者,在台湾有着传奇般的声名和事迹。然而内地的普通听众几乎不可能听到过他的声音,因为出道30多年,他第一张也是惟一的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刚刚于2005年4月录制完成。
2005年4月15日,胡德夫在台北开个唱,身处香港的龙应台得知,立刻乘机飞回台北观看。如她所料,演唱会当场,汇聚了一干功成名就的台湾文化人及蓝绿政治人物——而今在台湾,能让两个党派的政治人物平静并肩地坐在一起的,可能唯有胡德夫了。30年前,他们多半还是年轻的学子,就听着胡德夫的歌一路走来,许多人都是胡德夫的朋友。30年后,再坐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已分属对立的两方,只有当台上熟悉的歌声响起,他们还会用手去打同一个拍子,用心去哼同一个曲调。
这是传奇的胡德夫的力量。
现年56岁、被称为“原住民民谣之父”的胡德夫,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在1973年举办过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首唱《乡愁四韵》……他以歌参与了台湾那个动荡的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去年在纪念台湾民歌运动30周年的时候,台湾乐界办了一个盛大的音乐会,罗大佑开场,胡德夫压轴——也只能是胡德夫压轴,因为,与胡一起并称“民歌运动三君子”的李双泽和杨弦,前者于1977年意外离世,后者于1982年远走美国做了一名中医针灸师。其他民歌运动早期的关键性人物,有的做了唱片公司总裁;有的做了政客。歌手胡德夫的孤独是那么刺目。
《匆匆》不是一张最新创作集,它收录了胡德夫在过去30年间陆续唱过的12首歌,其中大多已是流行音乐研究者收藏的经典。专辑并非在专业的录音棚里完成,而是在胡德夫早年就读的淡江中学的小教堂里录制的,惟一的伴奏乐器是40年前那架断了两根弦的老钢琴。录制共花了两天时间,其间,胡德夫和朋友们时不时地谈笑,看着窗外的日影移动,很多废弃的母带里夹杂有蝉声。对于一张歌迷等待了30年的唱片来说,这样的录制过程多少显得有点漫不经心。
上世纪70年代,李双泽发出“唱自己的歌”的呼喊,胡德夫第一个站了出来,30年来以不断的现场吟唱和平均一年一首的超低创作率贡献着纯种的台湾“野生音乐”。70年代时,胡德夫一度是台北价码最高的钢琴酒吧歌手,但是在响应“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后,就再未把自己的歌用做商业用途。
1999年后,胡又以知天命的年纪再次折返山地乡间采集整理千百年来原住民的自由吟咏,并试图将其发展为能够独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海洋蓝调”(Hay-Yang Blues)。
当30年后胡德夫终于带着一张唱片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团队来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人们确信胡德夫依然挺立,台湾的“野生音乐”依然挺立。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胡德夫正在台湾屏东大武山的一个文化园区内,参加某原住民电视台成立一周年的台庆活动。虽然电话的信号很差,但仍可以听出胡德夫的声音与他满头白发的形象及沧桑粗砺的歌声形成明显反差,年轻坚决得就像一个小伙子。
“让人们能够觉醒起来,是我的荣幸”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上世纪70年代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你对那个时代的民歌是什么样的感情?
胡德夫:在原住民的孩子里,我能够碰到那样的时代,碰到席德进、李双泽那样精彩的人物,是我的荣幸。在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关心这片土地上有没有歌的问题,让人们能够觉醒起来,是我的荣幸。
中国新闻周刊:由你唱出的卑南族人自己创作的《美丽的稻穗》,成为台湾唱响的第一首“自己的歌”,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
胡德夫:70年代初,我在哥伦比亚商业推广中心,也是台湾最早的咖啡雅座唱歌。那里晚上不赶人,很多朋友拿着吉他过来一起唱。后来哥伦比亚就成为台湾民歌运动最早的摇篮。当时我们唱的都是英文歌,Bob Dylan之类。有一回,李双泽一定要我唱一个卑南族的歌来听,我搜肠刮肚后仅凭着模糊的记忆唱出了这一首《美丽的稻穗》。后来李双泽为我办了“美丽的稻穗”原创演唱会,还一张张地手绘海报。演唱会当天居然爆满,很多人从头跳到尾,这使我第一次看清楚了大家心里的渴望。
中国新闻周刊:李双泽对您的影响很大。
胡德夫:唉,李双泽这位同学,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有他盯着我走。有一次,在淡江大学一个演唱会上,李双泽在台上质问(同学们),“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歌?我们自己还有没有歌?”同学们竟然想不出来。他当场打碎一个可口可乐瓶子,说“《国父纪念歌》总会唱吧”,于是最后就一起唱了,场面非常震撼。那以后,“唱自己的歌”作为一句口号,一个思考,首先在校园里爆发了,很多学子开始在自己抽屉里写歌。
到明年,他就走了30年了,这些年来他的歌我经常唱,每次唱的时候都像跟他对话,我想跟他说,“兄弟,我们的岛还是那个美丽的岛,我也还在唱着。”
“我只能用歌说话”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民歌运动如火如荼,作为肇始者为什么你却选择离开?
胡德夫:我从小在大武山下的部落里长大,11岁到城里读书,念中学、大学、唱歌,一直觉得自己过得不错,不知道部落里的情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越来越多的同胞涌到城市去打工的过程,是我逐渐去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的过程。越了解,我就觉得肩上的负担越重。
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我参加救援工作,我站在那儿,周围到处是阿美族同胞的尸体,那以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为原住民争取权益这项行动中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也是你作为歌手的黄金年代,为什么决定弃歌从政?
胡德夫:当时觉得非走这条路不可。如果仅仅是做一个知识分子,我想我可以背转身去不看他们,但身为一个歌手就不行了。我不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好的运动组织者,我只是一个山上的孩子,我只能用歌说话。
这些年有很多朋友叫我作曲,做一首歌给多少钱,我不想那样。如果歌只是用来谋生就大可不必了。歌不出版也可以活着唱,集会的场合,歌是最好的表达。
胡德夫说他从不会没理由地去写一首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介绍每一首歌的来历、激发他创作的事件,是他最乐意表达的内容:《为什么》为海山煤矿爆炸而作;《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写原住民籍雏妓问题;《飞鱼、云豹、台北盆地》是对反核废料倾倒在少数民族地区运动的敬礼;《最最遥远的路》给在外求学的山地孩子们;《太平洋的风》想以自然风的尊贵激励原住民的自我认知……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从不为自己写歌?
胡德夫:呵呵,有一首《枫叶》是给自己的,写小时候一段暗恋的情怀。我觉得人一辈子都为自己活了,有时为别人活活也挺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歌曲的发表是否因你参与原住民运动而受到官方限制?
胡德夫:当局曾一度禁止我的声音出现在广播和电视上。后来我也不怎么把它当回事了,大地之上总有我唱歌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后你重新系统收集整理原住民民歌,推广Hay-Yang Blues,是否意味着把生活重点转回到了音乐本身?
胡德夫:是的。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唱歌就是生活,就是态度。经过几十年的人生,我更加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像音乐那样纯洁的东西了。
胡德夫,在“最最遥远的路”上
曹红蓓/文
《匆匆》貌似一张毫无野心的唱片,在音乐上和制作上堪称“原始”。然而,就是这张唱片,在问世的当年,即被海峡两岸数位知名乐评人列为个人珍藏年度最佳唱片,获得专业范围内的激赏。2006年,胡德夫凭此获得台湾金曲奖两项大奖,接着,又获得即将在下月举行的内地“华语音乐传媒大奖”4项提名。
当两岸业界纷纷抛弃当红偶像而将膜拜的对象转向这位活化石般的老者,事实上透露出的是一种普遍的惶恐——对身份遗失的惶恐。在这一点上,胡德夫因本身的原住民血统,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有着清醒的知觉和明确的痛感。而所谓的“业界”,却都曾在虚假的繁荣中蹉跎过多年。
胡德夫是台湾70年代的产物。那个时候,美国已全面介入越战,驻台美军上万,人们能够听到的音乐,要么是美军电台排行榜上的歌,要么是白光等从旧上海带来的歌。本地原创几乎一片沙漠,有才华的歌手要么到海外发展,要么由盗版和翻唱延续星途。大时代强烈呼唤本土文化的觉醒。
胡德夫、李双泽等,原来都是只唱英文歌的歌手,李双泽“淡江事件”代表着台湾流行音乐从殖民化向自由创作的转变。先是“唱自己的歌”成为时代的口号,知识分子第一次大批介入歌曲创作,开启了白衣胜雪的纯真年代,继而陈达的歌、洪通的画和云门舞集共同掀起“寻根”热潮,发动了对自身身份的全面追索。
然而在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爆发之后,商业的介入便迅速淡化了这种独立意识在音乐中的先行地位,当新的时代日、韩、欧美等各种席卷全球的音乐类型海浪一样拍打过来的时候,比胡德夫时代坚韧百倍的唱片工业中却再没有人能挺身抵挡。
在台湾音乐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内地原创歌坛,真正拥有“自己的歌”的时间更是短暂得昙花一现。
胡德夫献唱最多的对象,是来自山地的大专学生,很多当年的学生今天已经当了校长,对那时听到的歌还耿耿于怀。胡德夫曾经专为他们做过一首《最最遥远的路》,歌中唱到: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引向曲调绝对的单纯……对胡德夫那样的人来说,在最最遥远的路上,他是被选中的。
在最最遥远的路上,音乐感觉一流的胡德夫拒绝学习西方记谱方法,一生采取祖先留下的自然吟咏进行极缓慢的创作;在最最遥远的路上,坚持“活着唱”的胡德夫从未为了版税或修饰而进录音棚,以至于到现在还是一个被评为“听现场比唱片感动三百倍”的歌者;在最最遥远的路上,当同龄人都纷纷在光鲜的社会位置上“到站”,胡德夫却一度落到只能住在部落里以采集野菜为生。但,也正因为选择了一条最最遥远的路,绕过几十年的光阴,作为一个歌者的胡德夫才没有被时间吞噬而重新站在了人们面前。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6-7-18 11:58 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传奇歌手胡德夫:世上再没有比音乐纯洁的东西
传奇歌手胡德夫:世上再没有比音乐纯洁的东西
出道30多年仅出了一张唱片,他的演唱会却是台湾文化人及各路政治人物出席得最多的
★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6年台湾金曲奖的最佳词作和最佳年度歌曲颁给了一位叫胡德夫的人。这位银发满头、身形矮壮的卑南族歌者,在台湾有着传奇般的声名和事迹。然而内地的普通听众几乎不可能听到过他的声音,因为出道30多年,他第一张也是惟一的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刚刚于2005年4月录制完成。
2005年4月15日,胡德夫在台北开个唱,身处香港的龙应台得知,立刻乘机飞回台北观看。如她所料,演唱会当场,汇聚了一干功成名就的台湾文化人及蓝绿政治人物——而今在台湾,能让两个党派的政治人物平静并肩地坐在一起的,可能唯有胡德夫了。30年前,他们多半还是年轻的学子,就听着胡德夫的歌一路走来,许多人都是胡德夫的朋友。30年后,再坐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已分属对立的两方,只有当台上熟悉的歌声响起,他们还会用手去打同一个拍子,用心去哼同一个曲调。
这是传奇的胡德夫的力量。
现年56岁、被称为“原住民民谣之父”的胡德夫,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在1973年举办过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首唱《乡愁四韵》……他以歌参与了台湾那个动荡的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去年在纪念台湾民歌运动30周年的时候,台湾乐界办了一个盛大的音乐会,罗大佑开场,胡德夫压轴——也只能是胡德夫压轴,因为,与胡一起并称“民歌运动三君子”的李双泽和杨弦,前者于1977年意外离世,后者于1982年远走美国做了一名中医针灸师。其他民歌运动早期的关键性人物,有的做了唱片公司总裁;有的做了政客。歌手胡德夫的孤独是那么刺目。
《匆匆》不是一张最新创作集,它收录了胡德夫在过去30年间陆续唱过的12首歌,其中大多已是流行音乐研究者收藏的经典。专辑并非在专业的录音棚里完成,而是在胡德夫早年就读的淡江中学的小教堂里录制的,惟一的伴奏乐器是40年前那架断了两根弦的老钢琴。录制共花了两天时间,其间,胡德夫和朋友们时不时地谈笑,看着窗外的日影移动,很多废弃的母带里夹杂有蝉声。对于一张歌迷等待了30年的唱片来说,这样的录制过程多少显得有点漫不经心。
上世纪70年代,李双泽发出“唱自己的歌”的呼喊,胡德夫第一个站了出来,30年来以不断的现场吟唱和平均一年一首的超低创作率贡献着纯种的台湾“野生音乐”。70年代时,胡德夫一度是台北价码最高的钢琴酒吧歌手,但是在响应“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后,就再未把自己的歌用做商业用途。
1999年后,胡又以知天命的年纪再次折返山地乡间采集整理千百年来原住民的自由吟咏,并试图将其发展为能够独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海洋蓝调”(Hay-Yang Blues)。
当30年后胡德夫终于带着一张唱片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团队来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人们确信胡德夫依然挺立,台湾的“野生音乐”依然挺立。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胡德夫正在台湾屏东大武山的一个文化园区内,参加某原住民电视台成立一周年的台庆活动。虽然电话的信号很差,但仍可以听出胡德夫的声音与他满头白发的形象及沧桑粗砺的歌声形成明显反差,年轻坚决得就像一个小伙子。
“让人们能够觉醒起来,是我的荣幸”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上世纪70年代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你对那个时代的民歌是什么样的感情?
胡德夫:在原住民的孩子里,我能够碰到那样的时代,碰到席德进、李双泽那样精彩的人物,是我的荣幸。在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关心这片土地上有没有歌的问题,让人们能够觉醒起来,是我的荣幸。
中国新闻周刊:由你唱出的卑南族人自己创作的《美丽的稻穗》,成为台湾唱响的第一首“自己的歌”,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
胡德夫:70年代初,我在哥伦比亚商业推广中心,也是台湾最早的咖啡雅座唱歌。那里晚上不赶人,很多朋友拿着吉他过来一起唱。后来哥伦比亚就成为台湾民歌运动最早的摇篮。当时我们唱的都是英文歌,Bob Dylan之类。有一回,李双泽一定要我唱一个卑南族的歌来听,我搜肠刮肚后仅凭着模糊的记忆唱出了这一首《美丽的稻穗》。后来李双泽为我办了“美丽的稻穗”原创演唱会,还一张张地手绘海报。演唱会当天居然爆满,很多人从头跳到尾,这使我第一次看清楚了大家心里的渴望。
中国新闻周刊:李双泽对您的影响很大。
胡德夫:唉,李双泽这位同学,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有他盯着我走。有一次,在淡江大学一个演唱会上,李双泽在台上质问(同学们),“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歌?我们自己还有没有歌?”同学们竟然想不出来。他当场打碎一个可口可乐瓶子,说“《国父纪念歌》总会唱吧”,于是最后就一起唱了,场面非常震撼。那以后,“唱自己的歌”作为一句口号,一个思考,首先在校园里爆发了,很多学子开始在自己抽屉里写歌。
到明年,他就走了30年了,这些年来他的歌我经常唱,每次唱的时候都像跟他对话,我想跟他说,“兄弟,我们的岛还是那个美丽的岛,我也还在唱着。”
“我只能用歌说话”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民歌运动如火如荼,作为肇始者为什么你却选择离开?
胡德夫:我从小在大武山下的部落里长大,11岁到城里读书,念中学、大学、唱歌,一直觉得自己过得不错,不知道部落里的情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正是越来越多的同胞涌到城市去打工的过程,是我逐渐去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的过程。越了解,我就觉得肩上的负担越重。
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我参加救援工作,我站在那儿,周围到处是阿美族同胞的尸体,那以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为原住民争取权益这项行动中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也是你作为歌手的黄金年代,为什么决定弃歌从政?
胡德夫:当时觉得非走这条路不可。如果仅仅是做一个知识分子,我想我可以背转身去不看他们,但身为一个歌手就不行了。我不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好的运动组织者,我只是一个山上的孩子,我只能用歌说话。
这些年有很多朋友叫我作曲,做一首歌给多少钱,我不想那样。如果歌只是用来谋生就大可不必了。歌不出版也可以活着唱,集会的场合,歌是最好的表达。
胡德夫说他从不会没理由地去写一首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介绍每一首歌的来历、激发他创作的事件,是他最乐意表达的内容:《为什么》为海山煤矿爆炸而作;《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写原住民籍雏妓问题;《飞鱼、云豹、台北盆地》是对反核废料倾倒在少数民族地区运动的敬礼;《最最遥远的路》给在外求学的山地孩子们;《太平洋的风》想以自然风的尊贵激励原住民的自我认知……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从不为自己写歌?
胡德夫:呵呵,有一首《枫叶》是给自己的,写小时候一段暗恋的情怀。我觉得人一辈子都为自己活了,有时为别人活活也挺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歌曲的发表是否因你参与原住民运动而受到官方限制?
胡德夫:当局曾一度禁止我的声音出现在广播和电视上。后来我也不怎么把它当回事了,大地之上总有我唱歌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后你重新系统收集整理原住民民歌,推广Hay-Yang Blues,是否意味着把生活重点转回到了音乐本身?
胡德夫:是的。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唱歌就是生活,就是态度。经过几十年的人生,我更加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像音乐那样纯洁的东西了。
胡德夫,在“最最遥远的路”上
曹红蓓/文
《匆匆》貌似一张毫无野心的唱片,在音乐上和制作上堪称“原始”。然而,就是这张唱片,在问世的当年,即被海峡两岸数位知名乐评人列为个人珍藏年度最佳唱片,获得专业范围内的激赏。2006年,胡德夫凭此获得台湾金曲奖两项大奖,接着,又获得即将在下月举行的内地“华语音乐传媒大奖”4项提名。
当两岸业界纷纷抛弃当红偶像而将膜拜的对象转向这位活化石般的老者,事实上透露出的是一种普遍的惶恐——对身份遗失的惶恐。在这一点上,胡德夫因本身的原住民血统,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有着清醒的知觉和明确的痛感。而所谓的“业界”,却都曾在虚假的繁荣中蹉跎过多年。
胡德夫是台湾70年代的产物。那个时候,美国已全面介入越战,驻台美军上万,人们能够听到的音乐,要么是美军电台排行榜上的歌,要么是白光等从旧上海带来的歌。本地原创几乎一片沙漠,有才华的歌手要么到海外发展,要么由盗版和翻唱延续星途。大时代强烈呼唤本土文化的觉醒。
胡德夫、李双泽等,原来都是只唱英文歌的歌手,李双泽“淡江事件”代表着台湾流行音乐从殖民化向自由创作的转变。先是“唱自己的歌”成为时代的口号,知识分子第一次大批介入歌曲创作,开启了白衣胜雪的纯真年代,继而陈达的歌、洪通的画和云门舞集共同掀起“寻根”热潮,发动了对自身身份的全面追索。
然而在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爆发之后,商业的介入便迅速淡化了这种独立意识在音乐中的先行地位,当新的时代日、韩、欧美等各种席卷全球的音乐类型海浪一样拍打过来的时候,比胡德夫时代坚韧百倍的唱片工业中却再没有人能挺身抵挡。
在台湾音乐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内地原创歌坛,真正拥有“自己的歌”的时间更是短暂得昙花一现。
胡德夫献唱最多的对象,是来自山地的大专学生,很多当年的学生今天已经当了校长,对那时听到的歌还耿耿于怀。胡德夫曾经专为他们做过一首《最最遥远的路》,歌中唱到: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引向曲调绝对的单纯……对胡德夫那样的人来说,在最最遥远的路上,他是被选中的。
在最最遥远的路上,音乐感觉一流的胡德夫拒绝学习西方记谱方法,一生采取祖先留下的自然吟咏进行极缓慢的创作;在最最遥远的路上,坚持“活着唱”的胡德夫从未为了版税或修饰而进录音棚,以至于到现在还是一个被评为“听现场比唱片感动三百倍”的歌者;在最最遥远的路上,当同龄人都纷纷在光鲜的社会位置上“到站”,胡德夫却一度落到只能住在部落里以采集野菜为生。但,也正因为选择了一条最最遥远的路,绕过几十年的光阴,作为一个歌者的胡德夫才没有被时间吞噬而重新站在了人们面前。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6-7-18 14:50



胡德夫获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赏最佳国语男歌手
一边是民谣 一边是摇滚
华语音乐大赏中间由于种种原因,由大奖变成了大赏,但其偏好民谣音乐的一直没有改变,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音乐奖的显著特征之一。在这届的颁奖典礼上,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获得最佳民谣艺人和最佳男歌手,给现在的年轻乐迷认识好音乐的机会。胡德夫在颁奖典礼上携弟子各自演唱了一首民谣歌曲,没经修饰的自然音乐让现场的很多年轻观众听得非常温暖,情不自禁地跟着歌声打起了节拍。在享受民谣的同时,也让他们记住了这个30多年才发首张专辑的胡德夫。
崔健获得殿堂音乐家和太极乐队获得殿堂乐队也让人体会到华语音乐大赏对于摇滚音乐的偏好,一段温馨的民谣穿插颁奖典礼中间,在结尾处则是摇滚的放纵。太极乐队和崔健的表演,尤其是崔健,激情肆意地演出把人带回到一如和现在躁动的年代,不过,那个年代更多的是物质的躁动,而这个年代,则更多的是物质的躁动。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6-7-18 14:50



胡德夫获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赏最佳国语男歌手
一边是民谣 一边是摇滚
华语音乐大赏中间由于种种原因,由大奖变成了大赏,但其偏好民谣音乐的一直没有改变,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音乐奖的显著特征之一。在这届的颁奖典礼上,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获得最佳民谣艺人和最佳男歌手,给现在的年轻乐迷认识好音乐的机会。胡德夫在颁奖典礼上携弟子各自演唱了一首民谣歌曲,没经修饰的自然音乐让现场的很多年轻观众听得非常温暖,情不自禁地跟着歌声打起了节拍。在享受民谣的同时,也让他们记住了这个30多年才发首张专辑的胡德夫。
崔健获得殿堂音乐家和太极乐队获得殿堂乐队也让人体会到华语音乐大赏对于摇滚音乐的偏好,一段温馨的民谣穿插颁奖典礼中间,在结尾处则是摇滚的放纵。太极乐队和崔健的表演,尤其是崔健,激情肆意地演出把人带回到一如和现在躁动的年代,不过,那个年代更多的是物质的躁动,而这个年代,则更多的是物质的躁动。
| 欢迎光临 罗大佑音乐联盟网论坛 (http://luodayou.net/bbs2/)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