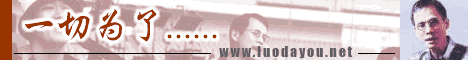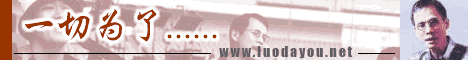
标题: 罗大佑:民歌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对往昔的追忆 [打印本页]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7-6-28 10:19 标题: 罗大佑:民歌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对往昔的追忆
罗大佑:民歌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对往昔的追忆
2007年6月27日 新浪娱乐
1、当时,在校园中流传的最广的歌曲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听音乐?校园里大家一起常常会传唱的是哪些歌曲?
罗大佑:早期都是一些西洋歌曲,或是所谓的流行国语与歌曲,那是被禁锢的年代,校园里面有些声音出来是后来的事情。
2、伴随着当年那些传唱甚广的歌曲,还有没有其它一些流行事物流传甚广,与音乐有关的?诸如:在人们的吃穿住行中和现代生活对比、反差巨大的东西。
罗大佑:当时音乐的代表,也就是象征校园的纯真,对自己生活与民族的一种内省,所以大家会看到特别朴素的感觉,这跟美国当年稍早的嬉皮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思考会想寻找自己的真。所以看看当时的衣着,简单的衬衫、牛仔裤。我这就这样上节目去表演,跟现在讲究的舞台效果是不同的,我们希望的是表现内在思考过的东西。
3、那个时候,校园的娱乐方式跟现在肯定相去甚远,请说说你们那时候,校园里学生们的娱乐生活。或请说说,你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最快乐的事情。
罗大佑:我认为本质是没有不同的,不过是形势改变了,我们用歌声自弹自唱,现在有科技帮忙,上KTV不是也差不多。当时常常忧国忧民,快乐就是在思考问题中不停的又发现问题。哈哈。
4、你所在的那个年代,在你以及和你同年代的创作人,歌手身上,你认为最珍贵的精神是什么?你认为哪些东西是值得传承和保留下来的?
罗大佑:民歌是生活,是一种态度,是文学的缩影,是情爱的告白,是简单的享受,是对往昔的尊敬与憧憬,是对不可得的过往的追忆,是年少轻狂,是交往的工具, 是一种流行,是反传统,是不受拘束的快意音乐行,是年青写真,是勇于尝试,是不悔的青春,是集体行动后的自醒,是承诺的懊悔,是追寻的怅惘……是空白的单纯,是默契,是生死与共的信任,这些就足够我们来思考在这社会上应有追求的价值,过去的创造在今日仍可以被适应的价值,这就是民歌。
对我来说,民歌曾经是那个百花争鸣。简单快乐的音乐创作及分享的年代的时代备忘录及见证。他们都是才华洋溢的大学高材生。文学造诣深厚。充满热情和一点点的愤世嫉俗及自怜。才得以无拘无束的创造。最后建构出华人流行音乐的广大基台。吴念真导演曾说:“我们这一代是供养父母的最后一代。也是被下一代弃养的第一代。“我们亦可以说”四、五年级是承先启后最辛苦又是最得天独厚的一代。只因我们和民歌一起成长,享受,共欢,而后等年龄渐长,收入稳定,五子登科后,再用剩余的心力,金钱去找寻,追忆,那曾经的一切。不管是失去远扬或仍紧紧握在心上的片爪鸿泥。如果时光倒流,青春重新再来过,我们又将如何?所有那时许下的未来志愿。计划是否会大肆改观,或是往事已矣,英雄无力回天?历史重演是幸福的吗?怀旧一定是美的吗? 过去就一定值得回味再三吗?还是根本我们就一直没能圆梦过?只是为谱新曲强说愁?往事如烟或不如烟,只有在每次的演出中,每人不停的拭泪,或低吟或大声唱喝,或倾听,或痴痴瞧望身旁人,手中紧握他(她)的手,是当年那好冷的小手,还是,于是我们演出完常到馆外去实地观察——他们紧握着手在馆外四周就这么走者,到咖啡厅畅谈一晚,坐在车上再回味的唱着刚刚的歌曲,大伙再约至卡拉OK,照演唱曲目一首首叫出来,澈夜抢唱至天明…… (有人激情后还怀孕了,竟还打电话谢谢制作单位——多年轻啊) 我们感怀的,是一段美好集体记忆的随风而逝,那记忆里有我们共同拥有,创造的年轻与幻想,符号已深烙,而散场电影才启幕……
10、现在,似乎已经不再是唱片的年代,黑胶唱片、CD卡带都成为了昨天的收藏品,唱片公司大多以出CD做宣传,靠卖彩铃挣钱,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来临对音乐产业和音乐创作的影响都非常巨大,移动终端更是改变了音乐的介质。对于目前华语流行乐坛的这种状况,你的看法是什么?或者说,你的感受是什么?请问,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大家似乎都在追求音乐形态的多元化,歌词中的人文创作该如何坚持下来,或者说保留下来?
罗大佑:当我是音乐制作人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商业的思考是必要的。如果他作为商业经营,也就必须要这样做。企业不赚钱也就无法支持其它社会的责任工作。这是平衡互动关系。世代的流行是社会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自我的觉醒是很重要的,可以扩延到整个工作、职业,当然如何坚持是很大的问题,但不是不可为,理想有多大,梦想有多远,发自内心的东西最容易感动人,如果可以感动人便不怕留不下来,就如同民歌如何写入生活、写入那个年代的青春。
12、现在,在校园中还是有很多年轻歌手在尝试创作,您对他们有什么希望?或者能不能给他们说点什么,鼓励鼓励他们?
罗大佑:这是一种过程,让我想起过去民歌手奋起的年代。当校园民歌独占台湾歌坛时,举办词曲创作及演唱的比赛蔚为风潮,当时的指标性比赛有金韵奖、民谣风、大学城,脱颖而出的都是顶尖好手,从包美圣、陈明韶到邰肇玫、王海玲、齐豫、蔡琴、苏来、郑怡、施孝荣、李建复、叶佳修等人,都是个中翘楚。为数不少的歌手后来投入幕后制作,随着时间流转,民歌已不再是媒体主流歌曲,浓浓的词曲情境,早已成为了一种“文化”!也希望他们共同能创造出这年代所属的文化,加油。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7-6-28 10:22
叶蓓:参与校园音乐创作义不容辞
2007年6月28日 新浪娱乐
 “大学生音乐节”专题采访——叶蓓
“大学生音乐节”专题采访——叶蓓
金兆钧:叶蓓你好,
叶 蓓:金老师好。
金兆钧:听说你现在又上学了,是吗?
叶 蓓:对,研究生。就是把时间再利用好。
金兆钧:你大学哪年毕业?
叶 蓓:97年。
金兆钧:上学的时候呢?
叶 蓓:你打听我岁数,我92年,我大学读了五年,在中国音乐学院。
金兆钧:今年已经是高考三十年了,我是第一届的,对于我来说,现在校园已经够遥远的了,但是还能想起点东西来。
叶 蓓:您现在还在学校当老师吗?
金兆钧:兼课嘛。
叶 蓓: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好。
金兆钧: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怀怀各自的“旧”。你当时专业是什么?
叶 蓓:声乐表演。
金兆钧:那时候肯定是学民歌了。
叶 蓓:对啊,唱得好着呢。
金兆钧:说说心里的偶像是谁?
叶 蓓: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彭丽媛、张也、宋祖英。
金兆钧:都是你们的师姐。
叶 蓓:对,我们倒她们的磁带,过来学,上课的时候听,去唱她们的曲子。
金兆钧:其他的呢?流行歌开始听了吗?
叶 蓓:从小学毕业开始了,特别早,因为我妈妈是音乐老师,每年学生不是有“欣赏课”吗,学校会给她一学期比如二百块钱的预算,会买好多好多的磁带,那个时候我记得磁带是五块钱到十三块钱不等,基本上不买CD,CD比较贵。我妈妈会买很多的古典音乐,比如莫扎特、贝多芬,还剩下一部分满足我的心愿。可能为了二、三十块钱的总量,我在磁带柜台,我记得在我们家门口商场的二楼把角的地方,在那一趴就两、三个小时,选我喜欢的磁带。因为钱数有限,所以我必须在这个钱里面选我最喜欢的。
金兆钧:你记得你当时最喜欢的吗?
叶 蓓:我记得我买过国内的像程琳的《熊猫咪咪》、张蔷的《爱你在心口难开》,港台的比如苏芮的、凤飞飞的、齐秦的、杨琳的。其实买的女孩(专辑)多一点,因为我喜欢听女孩的声音,可以对我帮助大一点。我记得喜欢的磁带……我们班有这种家庭环境也不错的,比如说他说你买这个,我买这个,我们回来拷。听断了之后,拿灯泡照着,拿胶一粘,把磁带再粘上,所以特别感兴趣。每个磁带外面做一个白色的纸封套保护起来,歌词都不要折,都是给它复音了,留着一张纸,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金兆钧:你听得还挺广泛的,不是说专攻一人的,你什么都听。
叶 蓓:对。
金兆钧:我说句比较外行的话,你不觉得你的专业在跟你听的流行歌“打架”吗?
叶 蓓:我不觉得打架。因为我18岁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努力考上这个大学,因为这个大学是我一直梦想进的学校,因为我妈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是拉大提琴的,子承父业。我妈就很喜欢,说能不能你学我们学校的东西。老师就开始教我唱民歌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想一定要勤工俭学,开始晚上下课都去PUB里唱歌,那个时候唱歌的时候就要选很多好听的歌,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爱好,特别有瘾。我觉得一方面可以跟乐队唱得特好听的歌,那时候给我们伴奏的是“零点乐队”,特开心。那时候都是去那为了自己的理想,有一个地方,音响好,一个月排练一次,你喜欢什么歌。我记得那时候是什么王靖雯、王馨平,《别问我是谁》就是那个时候,都会唱好听的,还有什么欧阳菲菲,那时候开始唱卡朋特。在考试之前的时候,老师说这段时间别出去唱歌了,会对你的方法有影响,因为学方法的时候不稳定,会打架,刚记好这个,又去唱那个,就会“打架”。作为听觉上说,觉得这个多好,离自己近,有兴趣。所以老师基本上好象很少管我们。
金兆钧:你们那个时代的同学,出去唱的多吗?
叶 蓓:不多。我们这几届好象就我,当数的比如民族乐器,他们会去酒店的餐厅,“伴宴”。民歌会去酒店的四川餐厅唱歌,唱三个小时,我也曾经替他们唱过一次,累死了,觉得。唱完一次觉得之后歇了半个月,嗓子不行了,不停唱《绣荷包》、《五歌放羊》,穿着旗袍,我觉得可好玩了。我出去唱流行的歌,同学们特别期望跟我一块去,想跟我看看社会上什么样,再加上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觉得手头上也比较松。
金兆钧:你们那个时候,能挣多少钱,就是串个场。
叶 蓓:一次150到200。那时候还挺有钱的,挺富裕的,我们那时候还有奖学金呢,基本上完全不需要家长给钱了,还倒给他们。我从18岁开始就交他们钱,我妈特高兴,说“孝顺”。
金兆钧:校园里,你们是专业院校,你能现在回忆你们那时候除了学习之外的生活,其他有什么特殊的值得记忆的东西,比如说同学爱看什么书、电影?
叶 蓓:我记得艺术院校的学生其实我觉得比较“清高”。比如那个时候94年的《同桌的你》特别红,《赤裸裸》、《回到拉萨》,但是在艺术院校里不放,基本上听的还是李宗盛,或者是崔健,基本上偏流行的东西不太听。在学校的琴房里,因为抢琴房抢得蛮厉害的,那个时候学校的琴房也比较少,恨不得打了饭之后,拎着塑料袋直接抢琴房去了。如果你能抢到一个琴房的话,你会觉得今天晚上没有荒废。如果今天没有琴房的话,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人家快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一晚上就虚度光阴了。但是在琴房的时候,学校的男孩和女孩经常会凑在一个琴房里,夏天买点草莓,搁在那个铁饭碗里,拿点白糖蘸着吃。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扒点流行歌,我记得他们扒的是罗大佑的《飘》,还蛮像的。还有李宗盛的好多类似像说话那样的歌,有几个高班的理论作曲系的男孩,挺起范儿的,当时在研究流行音乐这块。
金兆钧:当时服装上自己觉得有什么特点?
叶 蓓:服装上,那个时候男孩穿黑色的军靴,穿着短裤,穿着一个像崔健“红五星”的一个T恤,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是时髦的,现在这个看起来也是好看。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棒球帽穿一个T恤,穿一个大短裤,肥肥的,穿一个球鞋,有人说大夏天也不嫌热,好看。女孩好象大多数比较平庸一点,我觉得像我们艺术院校,琵琶、二胡什么的,基本上还是那种淑女的打扮,偶尔会有几个编上“麦穗”的头发的女孩,那个时候比较流行“麦穗”,编小辫,拿冷烫水,弄完之后第二天“爆炸”。那时候朱云就教我们,现在她不是在音乐台吗,她教我们“时长令”(音译)。每天早上她去上课,点名,我觉得一睁眼之后,洗脸之后就快到八点种,觉得她匆匆忙忙抹了一个“大红嘴唇”就去给我们上课点名去了,觉得特好玩。
金兆钧:中国音乐学院服装上还不是那么另类?
叶 蓓:不另类,我觉得另类的还是中戏什么的。
金兆钧:中戏、北大、清华,都有学校里唱歌的传统,你们学校没有吗?
叶 蓓:草地上没有。其实觉得很遗憾,没有去过理工大学,没有度过那样的时间。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得必有一失吧。
金兆钧:比如说当年的社会上的东西对学校里影响大吗,比如跟时髦,我记得有一阵大伙儿都读“琼瑶”,晚一点都读“席慕容”。
叶 蓓:读,所有的。包上语文的书皮,全看一遍。那是小学的时候看琼瑶。
金兆钧:92年到97年看什么?武侠看吗?
叶 蓓:不看。我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好象开始听电台了,因为上课之外看小说也无非就是言情小说,我就没怎么看过武侠小说,更多的时间听听电台、广播什么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刚有“91.5”,所以就每天晚上从这儿到那儿坐公共汽车坐一个多小时,拿上小的随身听,开始听。我记得“我是主持人盈风,轻盈的盈,风筝的风”,就这个“盈风”我一直想知道长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在我的记忆中,在我那段时间里印象太深了。还有那个男的叫李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印象,听电台还是听得多。国外的音乐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多一点介绍。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7-6-28 10:23
金兆钧:你什么时候卷进我们校园民谣里的?
叶 蓓:就是因为在PUB里唱歌,94年的时候,《同桌的你》那些人刚红完之后,我在那个地方唱歌,唱的是一个蓝调的歌,一个卡朋特的还有一个蓝调的爵士。高晓松他们去那玩,介绍了,中间的一个就介绍说他是写歌的,他又说请我以后能够帮他录小样。那个时候他说录小样,然后录唱片,后来真正让我录音了,有了第一家“麦田”,因为他是做校园民谣的,所以我就也是到这个圈子里了,就没有怎么想我的定位是什么,我应该往哪个方向想,就是这样跟着下来了,特简单,其实没有人好多人说的“星路历程”很艰辛,是不是有很多的不被人知的,好象没有,这块的经历其实还是挺顺畅的,我觉得。
金兆钧:那个时候跟晓松他们在一起,还能回忆起录音的生活状态吗?
叶 蓓: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都留着长头发,然后去录音棚的时候,我妈很担心他们是“坏人”,就跟着我。因为晓松经常是晚上十点种的时候打电话说叶蓓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说“打的”给报销,然后打辆黄色的“面的”,打着车去了。我妈说不行,我女儿不能这么晚去录音,哪有十点多钟才录音,这是真录音吗。跟着我一块去电台,一看录音棚里,张小安、老狼、高晓松都在那,这才放心。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的感觉都很敏感,就是录音的时候,尤其是我觉得老狼,我记得他录《青春无悔》的时候还哭了。因为他比我大六岁,他的感情是很细腻的,我觉得,在录音时候可以回想很多东西,再加上有一个女生是干干净净的,他是有点沧桑的,一对比觉得鸡皮疙瘩掉满地。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给我的影响特别大,他们会影响我听什么样的唱片。我记得晓松说你去听Susan的vige(音译),老狼说你去听Shedy(音译),就是给我介绍好多好多国外的唱片,不要老听港台的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一块去看演唱会的Video,在一块聊聊上学的时候的事,我记得我们第一组宣传照片是在清华拍的,高原给拍的,在大的拱门面前拍的照片,当时那种感觉特别“青涩”。所以其实到现在来说,格子的裙子、T恤和他头发有点点弯,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我的生活了,任何东西抹不掉,那个是我印象非常清楚的一段最珍贵的生活。大家都是为了拍什么东西,我记得宋晓辉,现在也不联系了,开着他的吉普车,载着七、八个人在后备厢里,拿着小马扎儿,照相机,自己化妆,请不起化妆师,拉到野三坡去,拍的各种各样特别感动的照片。你就觉得,因为我们的流行音乐那个时候也算中国起步的一段时间,正好是一个最流行的时候,所以大家的热情不一样,也不是很商业,当时的口号是“做良心音乐”嘛,那个印象还是挺深的。
金兆钧:现在回想起来,你算是稍微年轻一点,那个时代的感觉你现在回想一下,他们如果有某种精神,你能描述一下这种精神吗?
叶 蓓:就是做事。我觉得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觉得我们是做很多事是倒着捋的,比如做某个事我们先想到什么东西投放市场好,然后倒着往回捋。但是那个时候,包括我们做唱片封面,记得《青春无悔》那个唱片,封面是黑的,然后有一个艳粉的有毒的花,是拍的花拿电脑真做出来的。那个视觉上的冲击力,我觉得是很不商业的,但是这个东西你觉得很有冲击力,这个振动还是很大的。包括我们去录唱片,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pertools(音译)的录音棚,都是模拟带,都是大的录音房里倒、停,开始录,不行重来,没有像现在修音准、修节奏的非人性的操作,原来全是人性,这个地方加点口琴,那个地方比如加点小打,那个时候刘效松全是最棒的,我觉得全是精英们在一起为这个事努力做。包括我们在96年做高晓松音乐会,南京那站,真的大家都是全力以赴,这个事没有想过,反正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那时候刚读大二,没有想过什么市场、商业,什么有名,什么赚钱,还没有想到这些,觉得跟他们在一块能到这个圈子,是我想要做的事,还是挺理想的,那个时候是理想主义者。
金兆钧:说点生活上的事。你记得,比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搞对象都是去公园,一天省着吃一根冰棍,因为太穷了。你们那个时候,同学恋爱是什么样子?
叶 蓓:我们去后海荷花市场,吃香肠沙锅饭,或者是隆福寺的鱼丸汤,就是小吃,隆福寺那时候还有夜市呢,还有东华门夜市,不是现在的花岗石的地,是原来石灰地。一到晚上的时候,所有摊都出来了,我们都骑着自行车去。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画面还是蛮生动的,坐公共汽车也好,骑自行车也好。现在如果你想有这样的生活,似乎你也会觉得到处都在施工,也没有那个时候的清闲,也没有那个时候的心情了。那个时候能相约到一块,比如后海划船,现在也有船,租船要二百块,原来才三十块。荷花市场还有一些老艺人。
金兆钧: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离开“恭王府”是不是?
叶 蓓:对,附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完全没法出来了,我觉得我们的学校的地方比天津还远,前几年的北四环真的太“荒凉”了,从我们家出来坐车,坐一趟公共汽车,倒一趟无轨电车,下车还要倒小公共,不舍得坐地铁,地铁得两、三块。我们那个时候住校,我妈每次给我带一个饼干筒的“牛舌饼”,再带一个橘子罐头装的“雪菜肉丝酱”,怕我饿了,拿方便面吃,还会给我带上六个苹果,一天吃一个,到学校第一天就全被宿舍人分光了。我们到了北四环之后,基本上出来就有点困难,就特别不愿意回学校。那时候的学习就是被动性的学习,觉得学习主动性没有现在强。
金兆钧:现在有人说我们校园民谣的气质是知识分子,人文气质为主的东西。有人说其实当年比如校园民谣也是跟精神、产业之间良好互动的例子,有人说它传承了什么传统。你现在回头把你当初一批人在那个年代做的那一批音乐,来概括一下,不要受这几个条条的说话,因为毕竟它还是受到了相当、很好的一批受众,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文化事件,我也身临其境,校园民谣推出来之后,模仿、追随。你用你的感觉,重新归纳一下,我们九十年代中期的校园歌曲。
叶 蓓:我觉得从国外的流行音乐看,每个国家都有一段抹不掉的、很重要、很能影响受众群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像中国的校园民谣,因为我觉得中国地方大,有想法的人多,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商业操作手段,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市场需要这样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我觉得我不能说我们这批人“清高”吧,其实在我的骨子里,我觉得我们的起点是有文化的起点。其实我也很不愿意去承认流行音乐这个圈子有很多,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素质的这些,因为像晓松、老狼这些人为当时的这些东西还是有很多的奉献的,确实是影响了很多很多不同阶段的人。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里,这个阶段的产物势必会慢慢转型,转成一个更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在那个阶段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当时可选的唱片就是少,听众、学生都是非常善良、善解人意的,他们所听的东西都是抱着很好的态度听的,那种评判的东西很少。现在,比如电子、Hip—Hop种种东西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也会想是不是听众变了,市场也变了。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过程我是很愿意去看到,我觉得能鉴证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金兆钧:你现在又回到校园,很多人现在都在“批评”,晓松的说法是“墙低水浅”了,很平面化、浮躁化、社会化了,校园精神似乎失去了一个基础。你现在反正又回到你的母校读研究生,现在校园的气氛你还会感受一些,你对这个说法发表一下你的想法?
叶 蓓:其实我倒不同意晓松说的,我觉得不能用他当时的经历、要求现在的人,我觉得社会在发展,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在变的。包括学生们可以从互联网上了解更多的资讯,但是在以前是不行的,有的可能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才可以。我们原来出国填表,很可怕的是说你要查到某个学校对你的录取通知书的话,你需要去翻阅各种各样国外的书籍,你才能知道学校哪些录取是需要什么东西,奖学金是怎样申请的。但是现在容易到你可以直接在网上填这些东西,我觉得简单了很多。现在的人聪明的比以前早,为什么爸爸妈妈经常说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谈恋爱的学生可能是已经到11、12岁了,所以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了,因为时代在进展了,中国发展快了。我觉得所谓的“含金量”高也好,低也好,就是人有人自己的需求,你觉得这个东西有用我们就去。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向国外靠近,你主动去学什么东西,就是你以后有能量,就会去被释你的发光的东西。
金兆钧:如果要是按照你的说法,我们对现在局势不必过多的担忧,对校园民谣呢?比如我们这次“大学生音乐节”的口号是力图掀起校园音乐第三次(浪潮),阶段性的发展。有人不苟同,认为没有必要了,不能再回到高晓松时代,不能回到罗大佑的时代。你觉得还会出有校园的东西,还是说出的将来跟在社会上差不多,不会像你们那时候那么突出,成为一个单独的音乐现象?
叶 蓓:我自己想的是,我觉得接受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产生。我们的世界就像一个盘子一样可以“容忍”不同的“沙粒”在上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拿以前的标准搁在现代里,十年后学生的身上。因为现在学生喜欢的东西跟我们过去必定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生活背景。七零年的人跟八零年的人为什么有“代沟”,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背景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喜欢的东西如果能够被市场认可的话,也是一个好的东西。包括网络也好、电视选秀也好,我觉得是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过多的一定要把以前的东西作为完全的“克隆”copy到当今的时候,那样对发展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觉得应该是有新的东西,因为流行的东西跟古典的东西不一样,里面含有“快餐文化”的一个部分,允许这样的东西。究竟在这个市场上是不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才是真正需要大家用脑子思考的,怎样才能有持久性。
金兆钧:这次音乐节提出这么几个概念和口号,“向民族要旋律、向生活要歌词、向世界要方法、向未来要自我”。这几个口号,你能做点评价吗?
叶 蓓:不敢评价。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从当今的发展速度来说,我觉得跟 世界各大强国接轨的时间不会是遥遥无期的了,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应该有中国的特点,被世界接受。当你想你的产品为什么在世界上不被认可的时候,像“格莱美”,我们中国的音乐为什么总是不能被送到,但是电影在前几年,像张艺谋导演能够走向国际,为什么音乐还迟迟走不到,就是我觉得还没有找到能够被世界所接受的(方法)。这些口号其实是没错的,我觉得考虑问题其实要从不同的方面,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能被更多人看到,去接受的话,势必要寻找一个有“中国特色”,为世界接受的东西。如果从小范围来说,是不是能回到当时校园音乐的“辉煌”,那就是要看当前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具备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看“阶段性”的。
金兆钧:所谓的“80后”们,如果他们愿意来写歌,你能说说你对他们的希望吗?
叶 蓓:凭我自己的做事的风格来说,我觉得别把这个行业当成一个瞬间能够达到目的的一个行业,我是希望每个想要走进这个行业的人,抱着细水长流的目的,需要准备,需要做功课,这样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基础打得比较好一点。我也觉得,时代在发展,现在各个行业,比如美术、动画、音乐、MIDI编制等等这些东西,技巧性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先进了,如果好好利用的话,结合你的技术和现在的想象力、生活之后,我觉得非常好的。
金兆钧:现在的选秀搞得很热闹,就说流行音乐界出现了一个问题,最终由选秀决定它,还是音乐界的“精英”、专家们应该更好的控制歌坛的发展,现在争论比较激烈。你是作何态度?
叶 蓓:我觉得是市场,谁说得都不算,任何一个行业不是被一个人或节目控制,是市场判断你今后有发展还是到此为止。其实做电视本身的从业人员希望他们的节目好看,这个是他们的初衷,通过电视选秀出来的人希望艺术生涯长。真正说你具备不具备在一个市场细水长流走下去的能力,要看你最后的努力和你今后的市场。我并不觉得市场的东西一定是很商业、没有质量的,我觉得其实有可能达到一个好的定位,就是有市场、有技术、有好的口碑。
金兆钧:简单的把这几年流行音乐,你反正还在观察着,能不能有几句评价?
叶 蓓:近几年的市场不是很好,坚持大胆做音乐,投钱的唱片公司也在年年递减,原因有很多。比如网络出来的,冲击了真正做音乐的市场。电视媒体出来的,也来到我们真正做音乐的专业市场。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盗版,如果说所有的唱片公司正规的操作方法投钱、录唱片、卖唱片,这个循环还是蛮良性的,但是现在受到的冲击比较多。所以这几年出来的好作品不是非常的出色,没有前几年那么多。但是这是一个市场的转型和观望阶段,我觉得大家不用害怕,好的音乐还是会浮出水面,不要担心这个东西。娱乐行业永远不要把它当成一、两年的事,你有好的东西可以慢慢释放出来。
金兆钧:今年大家操办了一个“大学生音乐节”,选择了一个契机,一个是我们高考三十年,另外对于台湾的音乐来讲,他们也是三十年的一个发展,这样等于是从主办者角度讲,这个活动其中还有一个是选择新的校园歌曲的作品,或者想办法帮他们推广,可能还要出书,还有你们参加的两地校园民谣歌手的演出。用几句话表述一下对音乐节的祝福也好,期盼也好。
叶 蓓:我希望这次活动之后能够发现更好的作者和作品,我是希望能够为这个市场、行业“发光”吧。
金兆钧:今后有关我们的校园音乐,包括流行音乐,你毕业之后应当还会关注和参与吧?
叶 蓓:当然,这个是我义不容辞,也是我非常非常乐意的。
时 间:2007年6月22日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7-6-28 10:24
赵节:音乐其实很简单 真诚表达自己就OK
2007年6月28日 新浪娱乐

“大学生音乐节”专题采访——赵节
张亚苹:赵老师您好,欢迎您来我们“大学生音乐节”做客。首先问你一下,作为一个“校园音乐人”,能不能说说什么样的一首歌曲能让您想起您的大学时代?
赵 节: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可以给你特别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不止是大学了,就是中学的感觉、大学的感觉,学生时代的感觉,是有一首歌,叫《会有那么一天》。如果让我想起学生时代的歌,我有一首特别喜欢的歌叫《张三的歌》,后来蔡琴也曾经唱过,最早李寿全的一首歌。那里的歌词大概就是,“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我觉得这种感觉,在大学的时候和他们聊天,就说当时如果有一个男生弹着吉他给我唱这首歌的话,我可能就跟他走,特别纯真的感觉,蓝天白云,没有一点瑕疵的时代,就从这个歌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亚苹:这首歌是不是也反映了您18、19岁的青春岁月的状态?
赵 节:对。现在想起来18、19岁正好是高中考大学,尤其是刚刚考完大学之后,因为也松弦了,也没有太大的压力,离毕业、工作还很遥远,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人一辈子最放松的时候。
张亚苹:在您的大学时代,您最喜欢什么样的歌手或什么类型的歌?
赵 节:当时我喜欢的齐豫,马兆骏,前段时间已经过世了。当时它的一些,《那年我们19岁》这些歌曲,我们真的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里面留下了青春的印记。罗大佑我特别喜欢他一首歌,不是大家都熟悉的“90”,而是《恋曲80》,特别美好,那种境界特别美好。我记得有一次围炉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一起,他在台上,很多听着他的歌长大的人在台下,真的像一帮学生在那狂欢。就唱着《恋曲80》,想着自己美好的青春时代。
张亚苹:感觉您好像喜欢的很多歌曲还是校园气息特别浓的?
赵 节:其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是和时代有关。我们小时候,从初中、高中等等,当时也是台湾校园民歌比较繁荣的时期,得到的东西就是这些,你对音乐的理解,你所喜爱的东西,包括歌词表达的内容可能都会和你成长的阶段听的东西有关系。
张亚苹:我们上学的时候,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一般听收音机比较多。您上学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听音乐,是不是听收音机?
赵 节:收音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般宿舍11点熄灯,大家有不同的东西,有的收音机好点就贡献出来,就放在桌子上。11点有时候会有晚间的音乐节目,宿舍的“姐妹们”躺在自己床上,黑灯瞎火的,听着收音机里放出来的音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事,想起不同的故事,特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宿舍一个女孩有一个“大砖头”式的录音机,像砖头一样,旁边有一个几个扭,放一个卡带进去,我们把喜欢的磁带都拿来。而且当时我有一个习惯,有点“强迫症”,就是我喜欢的歌曲,一定要让我喜欢的人,能够理解的人听。当时的资讯并不是很发达,但是周围有一圈这样的朋友,于是会交换很多很多好听的磁带。磁带时代还是挺美好的。
张亚苹:我们上大学依然是听磁带,一直到毕业才会出现光盘、MP3什么的。
赵 节:对。其实磁带时代,有一次我妈妈说你要考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买磁带。当时的纯进口磁带很贵,平常的五块五,但是进口的需要十五块五,那个可能更早了,中学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妈给我买了一盘张国荣的进口磁带,而且特别支持我,她去单位的“双卡录音机”里,复制几份,给我特别好的朋友,同时把歌片拿出来,有复印机放大复音,送过他们。我觉得这个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好的礼物。
张亚苹:在大学时代,每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那么您在的那个学校,周边的同学,男女同学之间是怎么约会的?
赵 节:现在已经没有了,原来叫广院,现在叫“传媒大学”。每当提起的时候,还说广院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八号楼,是女生楼,是这样的一种形状,中间是进。
张亚苹:一个“U”口。
赵 节:对,我们在这边。每个礼拜三下午老师开会,经常会没有课,女生楼男生不可以进。当时有那种传呼器,一个那样的机关,上面有各种扭。比如说你要找301的,把扭往上一推,“301,谁谁过来,有人找”,就是很不现代,但是特别人性的东西。我们就经常在这个U口这里看上去,上面写着“学生公寓”,经常有男生,我觉得广院不仅是播音系声音好,我觉得大家声音都挺好的。在底下扯着脖子大喊,“谁谁谁下来”,上面“来啦”。这个特别纯真、简单的东西。有时候会停电,校园里当时有“核桃林”、几号楼的后面比较“隐蔽”,树比较老的地方。一停电就没有人了。我当时也没有男朋友,就点一个蜡烛,约几个朋友,弄点小酒,再弄点花生米,在那里写歌、唱歌。
张亚苹:我觉得越是原始的,很机械的方式,却能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回忆。
赵 节:对,特别纯真。
张亚苹:在当时,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让您记忆犹新的,比较震撼的社会事件?
赵 节:你要说社会事件,校园民谣就是社会事件了。其实如果要分析这个事的话,真的可以算社会事件。最近做一些歌的时候也会琢磨,社会整个的心态和音乐的关系。当时流行《黄土高坡》,然后到校园民谣,其实每个音乐形式都和社会、大家的心态有关系。为什么说“借半块橡皮”这种歌词,连工作了很多很多年的人都会有共鸣,这个是那个社会大家需要的怀旧,需要沉下来的感觉,不同的时代歌曲的形式不同。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黑豹”、“唐朝”,他们都比较火。现在想起来,好像那时候听摇滚的一些氛围和场合,包括“魔岩三杰”都是那个时候,大家情绪比较激烈,这个和社会上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事都有关系。
张亚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94年时候,央视有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专场音乐晚会。从那年开始,老狼一夜之间就成名了,我想他的作品对您的学校也好、您的创作也好,有没有什么影响?
赵 节: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时代,他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也在做什么事。《校园民谣》(一)首发的时候,我也在场,那些歌曲都是大家积淀了很多年,在这之前清华大学有创作歌曲协会,北工大有自创歌曲,也是类似协会这种,很多喜欢写歌的人在底下属于地下活动。之所以能够在94年的夏天爆发,是因为前年积累了很多时间,比如说十年,没有人都在听台湾的校园民歌长大,也尝试着表达自己的情感。时间长了之后,一点一点聚到一起,会有一个引爆点,94年只是引爆了而已。老狼他们只是这个学校、那个学校,很多学校当中其中一个学校的一批学生,后来还出了北大有个专辑《没有围墙的校园》、《校园新世纪》等等,有很多的校园歌曲,其实那个时候作品很多。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功利心,我只是要表达,我只是要唱歌给你听,这个是一个特别高的境界了。
张亚苹:在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很深的电影?
赵 节:我忘了是不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喜欢一个片子叫《海上钢琴师》,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托纳多雷,前段时间我还看,一个是里面的音乐特别好,可能有一些内敛的东西,包括人对社会的认识,还有一点点柔弱的东西。他也同时拍过《天堂电影院》、《西西里岛的传说》,大家都觉得那两个片子特别好,觉得这个是他哗众取宠,比较好莱坞式的东西,但是我挺喜欢的。又叫《钢琴师1900》,一个弃婴一直在一个大船上长大,一辈子都没有下过船,到最后船炸了,他还死在里面。如果从某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太热爱音乐,对人生没有把握。他说他的钢琴有88个键,黑白的,他能完全把握他。有一次他曾经想下船,但是看船的那边高楼大厦,他说88个键我可以掌握,但是人生太宽阔了,我没有办法把握它,于是他还是选择在船上死掉。里面有很多他和一个钢琴爵士大师斗钢琴,有三段,我没有没法描述,是有小感觉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我还喜欢《美国往事》,跟我喜欢的音乐和青春有关, 有青春情节啦。
张亚苹:我知道您父亲是学中文的,您的文学功底也很深,那您喜欢什么样的诗歌和小说?
赵 节:其实现在比以前懒多了,原来上学的时候我没有电脑,喜欢舒婷的诗,席慕容、三毛,那时候能接触到的就是这些,当时是比较畅销、流行的。当时我们作为播音系的学生我们还排练,自己找音乐,找特别动听的背景音乐,去念“故乡的歌是一支悠远的笛”,自己特别享受。其实我觉得读书那时候变成一种“娱乐”了,什么《致橡树》,当时能背好多诗,说起来特别有感觉。现在诗歌不像当时成为社会上一个主流的东西,不太提了,因为资讯太多了。
张亚苹: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比较有影响力的电视剧?
赵 节:在学校里没有电视可以看。那可能再小的时候,《渴望》那个影响力是万人空巷。
张亚苹:您那个时候有没有比较公认的偶像,比如像现在的周杰伦什么的?
赵 节:罗大佑和李宗盛,但是那种偶像和现在大家追星的偶像的感觉不一样。狂热当中还带着理智和敬佩吧,这个就是区别。或者我周围,我没有特别不理智,比较狂热的Fans。喜欢罗大佑、李宗盛,把他所有的歌全唱下来,对他的歌词倒背如流,这些就已经挺“偶像情节”的了,但是不至于做出更(过激),获取或者一定要在一起,现在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Fans事件,大家都挺平和的,大家比较能正确看待他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就到这为止了。
张亚苹: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流行的那种“歌本”?
赵 节:太流行了,我自己都有很多那种歌本。其实我们的字好像在歌本里练出来了。
张亚苹:初中的时候我也是喜欢很多的歌,买漂亮的本,把歌词抄上。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都会做这样的事。
赵 节:我现在在家里还能翻出来,那时候抄的不止是歌词,有歌词、诗、名人名言那种警示语、座右铭。如果说偶像的话,也会有,大家会喜欢港台硬性、歌星,还有那种贴画,不干胶的,整版,你把它撕下来,用来装饰你这一页,贴在那里。当时也有港台电视剧的歌比较好,把歌词抄下来,把主演的贴画贴在旁边。其实这些事挺青春、快乐的,还有很多文学青年,当时我也是在文科班,文学青年喜欢自己写小说、诗。上课传纸条的时候我觉得写得挺“做作”的,都写得特别有文学功底的样子。
张亚苹:什么样的事或机缘让您开始音乐创作,您是高三那年写的第一首作品《文科生的一个下午》吧?
赵 节:那只是一个歌。
张亚苹:我印象里,您那个歌是自己写的一首诗?
赵 节:对。当时《文科生的一个下午》是在高三的时候,因为是文科班要背很多很多的诗,有一天晚上回来我就写了一首诗,是下午有特别快乐的心情。那首诗的题目我还记得叫《有一首歌》,就写了一些骑自行车出去看到的一些事,一段一段的,前面还有括号写着“慢版”、“快版”等等。有一天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弹吉他,宿舍里好像就我一个人,坐在床边桌子面前,正好是西晒的,阳光进来,我觉得特别慵懒、愉快、开朗,看到当年高中的时候写的这个,就拨了吉他,就把它写成一首歌了,就是后来的《文科生的一个下午》。
张亚苹:那种感觉、情节可能是理科生感觉不到的。
赵 节:那不一定。其实我特别佩服那种懂音乐的理科生,我觉得比文科生全多了,又有这个脑子,又有那个脑子。
张亚苹:对您音乐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赵 节:应该是我爸。因为我爸不仅是对我音乐影响比较深,他培养了我日后一直尊崇的生活的原则,还有如何要求自己。音乐方面,我爸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大学学的是中文,后来音、体、美都教过,包括画画,都没有学过。只要给他一个乐器,不管是吹的,还是拉的,还是弹的,给他,他摆弄摆弄,就能弄出声来,而且弄出歌来。我记得当时初中,我爸弹扬琴、木琴,没有任何一个人教过他,就自己琢磨,也不是拿来就会了,就自己琢磨,都是自己学的。我的第一把吉他是我爸买给我的,当然这也是一种鼓励。他有一个朋友从苏联回来,当时还是叫苏联,带回一把吉他,家里挂着,我每次跟我爸找他玩的时候,我就把吉他拿下来,我说我弹一下那个,吉他的声音太好听了。我跟我爸说我想要一把吉他,我爸说你要考上重点高中的话,就给你买一把。为了一把吉他,努力考上重点高中。那是把红棉吉他,当时很贵,三十多。
张亚苹:你是专门学了吉他,还是像父亲一样?
赵 节:我就拿本书学的,所以我现在也不敢乱弹,我估计我弹吉他的好多姿势或者什么都不对,就是自己拿本书琢磨。
张亚苹:那等于是继承了父亲这方面的天分?
赵 节:天分也许有一点吧。但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真的想研究它,真的喜欢它。现在我在弹钢琴,也没有找老师,自己在摸,你会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完全是一种兴趣。
张亚苹:在您那个年代,跟您同一年代的创作人、歌手身上,你觉得他们最珍贵的精神是什么?
赵 节:真诚吧。前段时间还和李健聊起来,原来“水木”的,现在已经出了第三张专辑了。他的音乐就比较另人尊重,他就认为做音乐无论是什么时代,现在也应该用很真诚的方式对待。虽然大家说音乐已经变成了产品、商品,这样理解也没有错误,可以用一些经营的手段发挥更大的价值。但是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和你经营音乐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概念。创作音乐的时候一定要真诚,你是真的想有东西表达,而不是说准备写这样那样的东西,里面套点什么东西,加点什么佐料,放点“盐”、“酱油”、“味精”出来之后,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味,就像炒菜一样,你炒菜的时候带着感情出来的菜是吃的出来的。
张亚苹:是完全是为了一种倾诉?
赵 节:你在炒这个菜的时候,你不会想这要是西餐厅,我这盘菜卖多少钱。
张亚苹:有人说现在大学入学几乎没有了门槛,尤其是近十年,感觉校园没有了围墙,大学不再像过去“象牙塔”,是少数人才能进得去的地方,几乎跟社会没有了分界。您觉得现在校园的音乐和社会的普遍流行音乐还有没有区别?
赵 节:其实上次听了几百首歌,里面也有一些创作歌曲,也有挺好的。我觉得实际上是时空的距离越来越小,围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围墙越来越低了,看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多。包括一些社会上流行的音乐,其实我觉得这种大学生也是流行的很主导的力量,他们的思想比较先进,接受资讯比较快,反映得比较快。我觉得现在不是全民皆唱一首歌的时候了,我觉得挺可爱的,音乐风格越来越细化。可能你喜欢Hip—Hop,包括一些街舞等等也都比较系统,你是真扎下去了,这一条Hip—Hop线,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网上都能查得到,都能学得到,特别好。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在04年时候,我们曾经也出过一个合辑,是一个纪念辑。我看网上十几岁的孩子也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奇怪,我想十几岁,十几年前流行校园民谣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孩子。我觉得,实际上人是用个性和喜好分的,现在不用分年龄段或者是职业,而是个性上分,可能更合适一些。也有80岁喜欢校园民谣的,也许还有18岁喜欢校园民谣的,实际上和每个人习惯的表达方式、接受方式有关而已。
张亚苹:您觉得现在还有可能再形成一种新的校园文化的思潮吗?
赵 节:我对现在的校园里面大家都在做什么不是特别清楚,前几年还好做校园类的节目,现在没有接触,真不知道学校里会发生什么。
张亚苹:社会和校园完全的融合,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个不好的事?
赵 节:我不是中庸,谁问我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我不会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是一个哲理,有好坏、利弊,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闭塞,在象牙塔里,但是你会专心、专一、用心做一些你所喜欢的音乐等等。如果那个说是好处的话,现在这边大家融合得比较多,资讯比较发达,包括做音乐的手段越来越多,有很多上次听的小样里,好多都是大家自己亲手做的,也许不是学录音的,学编曲专业的,就凭爱好,有电脑、软件,就可以自己做出一首完整的歌来,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
张亚苹:现在有很多“模仿”,还有追星是一种“堕落”吗?
赵 节:不是,很多东西需要一个过程。小时候我们写东西也会模仿“冰心”她老人家文章的文风,有一段时间可能是模仿,等你写多了,再加上自己的感受,吸收的东西多了之后,你会慢慢发现,你的东西一点一点在形成。音乐也是,你可能想模仿周杰伦,你在模仿的过程中你在思考,你要想怎么样做得特别像,他的节奏是什么样,里面用的弦乐是什么感觉,你都在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摈弃掉一些太“他”的东西,里面出来了一些自己的新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你回头的时候,你发现你写的东西已经不是模仿,而是你自己的了,这个不是一种“堕落”,是一种“学习”。
张亚苹:这次我们“大学生音乐节”的口号是“向民族要旋律、向生活要歌词、向世界要方法、向未来要自我”,您如何评价?
赵 节:这个挺好。我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向民族要旋律”这个东西,最近我们要做一些歌,所以在研究一些歌曲,包括港台和内地,现在有民族调式的东西越来越多,包括周杰伦会把很多武生调式的东西放进来,你会觉得大家身上流的血是中华民族的血,你会觉得和这个音乐特别贴合,很舒服。包括像《江南》这种歌曲,听起来有点很洋,但是实际上旋律真是民族的调式。不一定要“武生”做音乐,但是这个口号特别好,真的把我们的很小精华的东西留下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文化大学”的人讲音乐,他讲的是“尺八”,一种日本的乐器,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箫”,他们都会这样学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古老的调调丢掉呢。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7-6-28 10:25
张亚苹:您对现在校园里尝试创作的年轻歌手有什么希望和告诫?
赵 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希望和告诫了,最重要的是真的要表达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脑子里不要有太多的思考和期盼,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拿出来的东西,可能真的是带“才华”的。现在我会听到很多的小样,你说技术没有问题,唱、声音的处理都很认真,但是那个东西像“匠人”的东西,不像很有才华的人的东西。当时我印象特别深,高晓松唱《恋恋风尘》比老狼唱得好,有一次我们在玩的时候,高晓松没有嗓子,大家特别开心的时候,他拿把吉他,当时留着长头发,一副“颓废青年”,但是还带点小浪漫的样子,说我们唱首歌吧。那时候老狼还没有录,他就唱《恋恋风尘》,弹着几个音,一唱,大家都陶醉了,因为那是用心在唱,不是用嗓子。所以我觉得音乐里最重要的还是真诚,是表达。如果你写东西的话,希望你自然而然的,想把你表达的表达出来就够了,不要想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这样会闻到另外的味道。
张亚苹: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选秀活动,有人说选秀选出明星,却选丢了音乐,您怎么评价?
赵 节:我觉得也没有怎么选丢了音乐吧,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说。选秀里大家唱的是以翻唱为主,偶尔有一些原创。我自己越来越平和了,对于很多没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音乐的人来说,选秀活动里的一些歌,从电视台来说他们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安排,对于歌手来说,他必须喜欢才会好好唱,这些歌就有更多的传播渠道,从他们的嘴里。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有一些大家很熟的歌,比如歌手自己弹着钢琴唱,对本人的诠释,或者是乐队改编,一个Hop的歌搞的有一点爵士味道等等。其实在选秀过程中,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慢慢的又进行了一次推广和宣传。说选丢了音乐,我不知道是为什么,除非是原创的比赛吧。当然还是希望选秀活动当中能有更多的原创的东西,自己的东西。通过这种选秀活动,把自己的东西推广宣传的话,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事,因为它毕竟具备很好的宣传渠道。
张亚苹:您怎么评价现在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
赵 节:有一句话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点这个意思,越来越多的音乐形式被大家接受。除了“百花齐放”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跟中国人普遍的音乐素养和音乐欣赏标准有关,还是比较大流行的东西,尤其是数字音乐。现在我在做数字音乐的工作,包括产品的“加工制作”,其实就是做歌啦,和音乐现状的一种分析,数字音乐的分析,大家还是喜欢大旋律,线条比较美好,还是比较单旋律的东西,像钢琴、吉他这种和声的乐器都是西方的,中国笛子、箫单旋律的东西,这种乐器还是比较多,可能是我们必须习惯于这种走旋律的东西。所以现在最为大众接受的还都是旋律感比较好的东西。
张亚苹:您会为大学生校园音乐的复苏和回潮做些什么?
赵 节:我觉得特别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我相信我当时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不一样的,我当时吉他里出来的就是蓝天、草地、美好、单纯、象牙塔,现在的大学校园越来越复杂,音乐形式也复杂了。但是没有关系,里面的歌是一样的,那就是我告诉你我唱歌给你听,这个是没有变的。所以,如果有哪些需要我们能做一些什么事,比如说包括这次活动,去听大家的一些东西,一些新歌,首先我们自己能够了解,如果能够从里面出来一些真正的还是校园歌手的人,我觉得会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学校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虽然离社会离的比以前近了。
张亚苹:您能讲一件您上学的时候和音乐有关的事?
赵 节:这个是我亲身经历吧。就在上学的时候,讲个郁冬和老狼吧。后来我曾经在一次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当时我们会经常在一起玩,弹琴、唱歌,有一天下着大雨,我和我同班同学从广院出来,坐1路到广电部门口,郁冬和老狼在马路的南边等我们。我们下了车之后,就打着伞,他们两个人也是往西走,我们在马路这边往西走,就是两把伞平行移动。到南礼士路口那边,最让我想起来特别高兴和难忘的,其实那首歌很多人都忘了,是郁冬写的一首歌叫《相约》,当时是潘劲东唱的,还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那个礼拜,正好是这首歌在北京音乐台排行榜打榜第一名。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娱乐,不知道是一毛钱还是五毛钱的硬币,我忘了,广电部门口有一个电话亭,下雨我们躲在电话亭里,很挤。郁冬说让我们来听歌,就拿起来一个硬币塞进去,拨了一个声讯台,那时候声讯台很发达,拨了号之后,里面说按1号键收听什么歌曲,我们就按了郁冬那首《相约》,潘劲东唱的。“是一个夏天的夜,我们悄悄的感觉……”,那个歌也很好听,每扔一个硬币就给这个歌投了一票,现在想起来那种感觉真的挺浪漫的,几个喜欢音乐的孩子,就是那样的感觉。前两天一个新浪的朋友想写一篇文章关于当年校园民谣里面的人,就提到郁冬,其实他是特别有才华的人,大家公认的。而且他说老狼说我们给郁冬出一个纪念专辑吧,我说郁冬还在呢,出纪念专辑干什么。《来自我心》,还有他自己写的《离开》,当时在正大有一张专辑叫《露天电影院》,里面有一首歌叫《时光流转》,“时间就是那么简单,轻易地改变了我们笑脸…”,他写的词也特别敏锐,他和高晓松两个人感觉不一样,郁冬更扎到内心里去。表面上好像不华丽,挺简单,我喜欢《来自我心》里的一句词,“任凭这天空越来越湛蓝,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这两句很简单,自己琢磨去吧。
张亚苹:您在大学里参加过什么活动?
赵 节:1994年5月12号,可以说中国校园民谣、校园歌曲、校园创作者们一个大聚会。当时是在北京工业大学,《校园民谣》(一)专辑发布会已经发过了,他们那边有一个叫“PMC”还是什么,就是“大学生校园自创歌曲协会”,邀请北大、清华、金融大学等等,北京有十几个高校,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文艺活动积极骨干,每个组唱两首歌,后来大家所知道的人在那台晚会上都出现过。包括老狼、高晓松、郁冬,现在的贾南和崔文斗,他们当时不是一个学校的,包括北大的一些学生。那台晚会之后,印象更深的是,我们在礼堂门口的草地上,有人搬了几箱啤酒,有人买了几条烟,大家穿着仔裤,坐在草地上,围成一个圈,有一把吉他在圈里轮。你唱完了,该你了,你唱你写的新歌。所以我连日子都记着,后来这天被定为“护士节”。
张亚苹:您用最简短的语言说说对首届“大学生音乐节”的期望和祝福?
赵 节:我期望能够写出你心里真想写的话,你真想唱的歌给别人听,这就够了。音乐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是用来感受,而不是用来炫耀,真诚表达你自己就OK了。
时 间:2007年6月23日
作者: 追梦人 时间: 2007-6-28 10:29
大学生音乐节论坛两岸交流 台湾音乐人期待歌会
2007年6月27日 新浪娱乐
王梦麟: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的年级比较长一点,我叫王梦麟。这边我要先跟这位主持人先问候一下您好,刚才您说过“我们面目全非”,可是我刚才跑到厕所里照了两次镜子,我才发现,实在是有点面目全非,是因为长了很多公斤的肉吧。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面目全非”,谢谢!
潘越云:各位现场的嘉宾,还有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主办单位,还有(王)祥基哥,大家好,我是潘越云。希望我不是那个“面目全非”的。不过今天很开心,而且我跟两位好朋友一起在这边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记者会。希望这次的演出,我们既期待又开心,又很兴奋!
叶佳修: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叶佳修,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碰面。我想,如果说有哪些话要说的话,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到现在,还继续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朋友们,为了共同一个目标努力,就是把我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和那个时代的生活透过文字,透过音乐,传递给以后的人。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我想刚刚提到的“面目全非”,跟我是完全没什么关系的,因为我18岁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就是因为我从小在乡下长大,长得也非常“面目全非”。所以我写的那些歌曲比较偏向,比如《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就比较偏向于大自然,因为每次照镜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大自然比我美多了。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尤其这个时代的朋友们,大概比较少接触大自然,我一直觉得大自然实际上我们必须要多多接触,能够多反映给所有听众的话,也是非常好的。
潘越云:各位现场的嘉宾,还有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潘越云!这次演出对我来说,即期待又兴奋,大家会听到很多的歌手都是原创、原唱的歌手,很期待这次的演出。我唱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好了,这是罗大佑的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还有我后面有两位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跟着我们一起。
叶佳修:晓松,非常感谢你刚刚给我问问题。尽管它就算是翻版的,我也非常高兴。你刚刚演唱真是相当的好,尤其是我看(罗)大佑都比不上你啊。感觉上,我们都感觉你好象来“踢馆”的感觉,所以维护我们的尊严,再送回去一首歌好啦。
作者: 大盛 时间: 2007-6-30 19:08
怎么没有大佑的照片呢?
| 欢迎光临 罗大佑音乐联盟网论坛 (http://luodayou.net/bbs2/) |
Powered by Discuz! 6.0.0 |
“大学生音乐节”专题采访——叶蓓